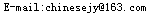2002年6月15日,李某被例行盘查的西单商场派出所民警发现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随后被羁押。在交待了违法事实后,被取保候审。
2002年9月26日,李某与其他三名同事一同在西城法院接受审判。候审时她们情绪很轻松,显然以为没什么大事。
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李某等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件罪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成立。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据此,法院处理李某有期徒刑10个月。
按语:西单中友百货商场2000年制定了聘用导购“限35岁以下北京市城镇户口”的规定后,一些导购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纷纷购买假身份证蒙混过关。截至到昨天,被立案审查的25名购买了假身份证的导购,已有24名被西城法院以伪造身份证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6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拘役。
又:昨天下午,记者从中友百货人力资源部获悉,该商场目前已经取消“限35岁以下,北京市城镇户口”录用规定。不过,记者还了解到,类似的规定在许多单位依然存在。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案例所反映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李某等人购买假证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且不说法院对此案适用的罪名错误,她们为什么这样做?用人单位作出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合法?更是我们应当深思的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或是原谅李某等人买假的行为,因为刺激行为人产生行为动机的因素一般来说不能成为刑法上免责的事由,即使成立刑法上的免责事由,也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治安处罚之责任。但是,从法理上讲,一个罪名的成立必须符合法定要件。我国刑法上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备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伪造”是无身份证制作权的人员之作虚假的居民身份证:“变造”,指用涂改、擦消、拼接等方法,在真的居民身份证上进行变更,改变姓名、年龄等事项内容。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李某等人购买的行为未被包含于其中,认定其行为构成伪造、变造身份证罪显然不当。同理,她们的行为当然也不能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她们实施的是非法购买假身份证和假户口簿的行为。假户口簿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争议。即便可以认为户口簿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她们的行为也只能认定为买卖假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和买卖假身份证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在刑法中没有被明确规定为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她们定罪量刑。有的地方法院把购买假证的行为解释为伪造行为的共犯,这在刑法理论上也难找到依据。因为当事人一方的故意内容是“卖出”而“赚钱”,另一方的故意内容是“付钱”而“买入”,故意的内容的指向相反,成对合关系而不是相同关系,这正如商品买卖,交易的双方各行其是,不存在“共同做生意”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可以认定买卖假证的当事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那么,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也不应当追究李某们的刑事责任。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一般人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有期待可能,则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应当免除其刑事责任。1具体到本案中来,在李某等人面临失业危险的情形下,期待她作出合法行为即不去买假身份证和假户口簿,可以说是强人所难,而“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的格言2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正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基础和免除无期待可能性者的刑事责任的终极原因。所以,对李某们以此种身陷困境的情况,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笔者认为,对李某们的违法行为,作出治安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但作出刑事追究,很难说具有正当性。以上是从刑法规定作出的实然性分析。
就中友百货商场的规定来讲,值得研究的是,其内容是否与我国宪法和劳动法相冲突。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由于法律固有的高度抽象性,仅仅从上述规定来看,我们很难对上述问题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平等就业的原则,即劳动者只要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用人单位就应当为其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并且坚持同工同酬。应该说,这一原则的主要方面是用人单位必须平等地向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并且在劳动者符合录用条件时-仅指劳动者具备必要的劳动能力及劳动技能和不具备某些否定性条件时,用人单位应当在符合劳动者本人愿意的前提下,与之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的决策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权力决策和行为是与宪法权利相冲突的,是有悖于人民利益和人民权利实现的,为人民所痛恶的充斥于社会中的土政策的大量存在就是例证。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考察一下,在我们社会中,究竟有多少权力性政策和行为是同宪法权利相吻合的,又有多少权力性决策和行为是同宪法权利相冲突的。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法学界、法律界认真考虑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就业实际上受到居住地域和身份的双重限制。农村居民只能种田耕地,城市居民不能下地干活(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上山下乡”以外)。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人为的禁锢,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少数城市居民也能到乡村开办实业或从事农业生产,但禁锢尚未彻底消除。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带来的福利、求学、就业等权利的差别仍然是悬殊的,大量单位关于“就业必须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规定、一些政府官员关于在城市“划出区域让外来人员集中居住以便于统一管理”的主张和个别城市部分市民“不要让打工者乘座公交车”的呼吁就是明证。
上述禁锢的解冻是市场经济观念影响的结果,而禁锢的固守则是宪法观念缺失的结果。国家乃举国公民之国,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某一省市、某一城市之公民;国家的任何城市不是某一省市居民的城市而是全国人民的城市(特别行政区是历史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例外);首都是全国公民的圣地。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到自己向往的城市居住、生活、学习和工作,适者生存,不适者离开。这是现代宪政应当树立的与就业权利的实现相适应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理念的引导下制定的制度,才能保障公民流动-实际上就是迁徙的自由和劳动权利-实际上也是义务的实现。没有这样的理念,公民的平等就无从谈起,“制度”逼人违法犯罪的现象就无法消除。
历史上争论多年的利与义的矛盾问题,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的协调问题。舍身取义,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利益、更根本的利益,如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使个人局部的利益、暂时的利益、非根本性的利益服从一个更大的整体利益、长远的利益、根本利益,这就是“义”。宪政的利益和宪法权利,可以归结为“义”或“正义”,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即“利”或“效益”。关于正义和效益的协调问题,实际上可还原为利益与利益的协调问题。法调节利益关系的矛盾,实质上也就是调节并缓和了法与正义的矛盾。但调节的结果,应当是“利”或“效益”得到满足,“义”或“正义”得到伸张。换言之,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消就业身份与地域的限制,绝不会妨害市场主体获得应有的效益,同时又有效保障了公民权利的实现。这是从法律的应然性作出的分析。
从法的实施效果和法的引导功能上讲,“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又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3也就是说,法律应该保护和引导人民追求正当权益。而本案的处理,在实实在在伤害了李某们的利益的同时,很难说能引导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传递的信息无非是:“想在城市就业吗?先合法取得城市户口和城市居民身份证吧!”而这恰恰是强人所难。因此,法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效果说明,谴责并引导用人单位彻底撤除违反宪法的藩篱,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1 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4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227页,法律出版社,1999。
3 参见[美] 洛克著:《政府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