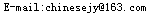1.“正雅典精神”和“负雅典精神”
什么是“希腊精神”?那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半岛上的一些“城邦国家”体现出的社会精神。其实,那些为数众多、大小不等的各个城邦国家,各自具有的社会精神相差很大,粗略划分一下,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
斯巴达的政治是一种贵族寡头的统治,真正掌握权利、制定决策的是五个长官(Ephorate)。贡斯当说:“斯巴达政府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贵族政府,五长官团的权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此,他们的特权会变成某种不堪忍受的暴政。”1强调纪律,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斯巴达以军事立国,也就是说,斯巴达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夺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或其他形式的被压迫者。斯巴达的面积在所有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大,这就是对它如此执着于军事事业的回报。而斯巴达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当然就是斯巴达人,他们只占斯巴达社会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第二个等级叫作“周围的居民”,他们是那些自愿臣服于斯巴达的人群。第三个等级就是“苦力”或隶农,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的状况。
事实上,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以军事立国是最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简直可以说是一条“客观规律”。在以后的一、两千年里,斯巴达人的行径被无数个其他民族重复着:雅典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高卢人、盎格鲁-萨克逊人、突厥人、蒙古人、斯拉夫人、维京人、东征的十字军。他们都曾经去征服别人,然后占有别人的土地,把别人变成奴隶或隶农;当然他们自己也都曾经被别人征服过。他们的这些行为都是无师自通的,就像吃饭一样。在当时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一个民族或一个集团如果想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只有两条路:种地和征服别人。种地安全一些,但辛苦而且所得甚微,还很可能被别人征服和奴役;去军事征服别人固然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行业,但回报也高。一场成功的战争既增加个人财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隶农、贡赋和土地,生活马上就可以上一个档次。利用肢体力量去攻击其他动物是动物界最常见的现象之一。早期人类发明了武器去攻击别人,攻击成功后攫取对方的财富,这种行为模式和动物的行为模式相差并不太大,人本来就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动物变来的。所以,凡是以农业(比如5世纪的日耳曼人)、渔业(比如公元1000年以前的北欧人)、牧业(比如中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这样一些以不需要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为主体的社会,从事生产和从事军事征服是同样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农业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军事征服十分频繁,从中国的历代王朝到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军事征服形成的。对此,孔德说:“所有理性的对政治的研究都证明人类具有一种原始性的对军事生活的倾向。”2 他认为:“军事活动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最简单最便利的手段。军事手段持久地、广泛地被传统社会的人们使用,说明它对于当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功用。”3 可以说,在当时十分低下的物质生产力状态下,战争成为了一些民族的“生产力”。
当然,这些民族可以向比尔·盖茨学习,向麦当劳学习,进行商业的而不是军事的扩张。可是,一直到14、15世纪,欧洲人都根本不知道现代工商业为何物,就像19世纪的慈禧太后不知道电灯为何物一样。人类发展工商业,要比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困难不知多少倍。但没有工商业,人仍然要生存、要发展,仍然想过舒服日子,而且想过一种有优越感的生活,没有谁会甘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苦日子、乃至做农奴。所以那时的欧洲人,还有西亚人、北非人,只要对生活有追求的,就是要打仗。打仗最光荣。从罗马到巴黎,那些雄伟壮丽的凯旋门都是为纪念打仗成功而盖的。
在欧洲历史上,工商业是在农业和军事这两种占压倒性地位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夹缝中逐渐地、极为艰难地生长出来,直到近代,它在欧洲才基本成形。只有当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工商业不再是社会中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性行为模式时,人们才开始选择:从事农业呢?还是从事工商业呢?还是去打仗呢?西方中古社会经济史权威汤普逊(J.W.Thompson)描述公元5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时说:“他们真是做一天吃一天,食粮是他们永远存在的问题。人口的数量太多,不可能由贫瘠的土地维持。由于情势所迫,他们变得不安定、飘泊和好战,他们实行杀婴和进行战争。”4他们最终在穆罕默德的指引下,成就了一番阿拉伯帝国的伟业。今天,阿拉伯国家当然不再需要打仗了,她只要使劲儿开采石油就行。这是因为,分工协作的工商业已经在今天的地球上成为了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这样,选择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并加入进去,往往好过进行战争。
所以贡斯当说:“战争的出现先于商业。战争与商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的两个不同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东西。经验引导人诉诸商业。经验向他证明:战争,即运用自己的强力反对他人的强力,使他可能遭受形形色色的障碍与失败,而商业则是求得他人权益符合自己适当权益的一种较为温和但较为确定的方法。”5 生活在18、19世纪之交法国的贡斯当宣称“一个商业代替战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6
而雅典精神则和斯巴达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军事性比斯巴达弱很多,而且它的商业十分发达。她是彻底的民主政治,并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哲学。在当时几万(也有学者认为是十几万)雅典公民中,他们的社会观念是自由、乐观、世俗主义、理性主义的,为人的肉体和思维感到骄傲,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说个人要服从什么的话,他只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意志。雅典人的宗教也是看重现世和注重实际的,只服务于人的福祉。雅典虽然有僧侣,但没有教会主义,而且雅典的僧侣阶层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雅典人从没有让僧侣们用他们的教义来限制思想自由。雅典人尊崇智慧,尊崇自由探究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领域不能自由探讨,没有什么领域可以在理性探究的范围之外。理智高于信仰,逻辑和科学高于迷信。显然,我们一般说的作为西方文明传统的“希腊精神”,绝不是指斯巴达精神,而是指“雅典精神”。因此,准确地说,本文的题目应该是“雅典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吗?”
为了更为明确,我把雅典精神又称为“正雅典精神”,以和“负雅典精神”对立和对比。所谓“负雅典精神”,那就是严格地恪守某种宗教教义或思想学说,贬低人的肉体和思维的价值,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在政治观念上,奉行君主集权,并有一个强大的僧侣集团对君主集权提供支持。在奉行这种精神的社会体中,这种精神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扩大国家权威和提高教士地位的工具。
从欧洲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19世纪以前的整个欧洲,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只在公元前5、4世纪、在雅典这一弹丸之地闪现了那么一下,虽然在后来中世纪一些欧洲的自治城市里,也存在过程度不等的民主,但都不如雅典的民主完备充分。较为充分的民主制在欧洲的下一次出现,是在19世纪的荷兰和英国。从欧洲摆脱原始文明直到近代之初的两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政治状况的主流是专制国王、战争、人身依附、骑士、贵族、农奴,我把它们称作: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力量造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它和民主这种通过每个人的自愿结合造成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正好相反。同样,欧洲开始使用理性进行思考,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也是自近代始,并且和尊奉信仰的基督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2.正负雅典精神分别属于近现代欧洲和古代中世纪的欧洲
近代以来的西方人,还有很多非西方人,谈起雅典精神,都是充满崇敬之情的。德国诗人雪莱说:“我们(注:指西方人)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是植根在希腊。”但美国的世界史权威伯恩斯在引述完雪莱的这番话以后,冷静地指出:没有哪个清醒的学者会接受雪莱这番有着太多感情色彩的话7。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不是那么简单。西方精神,是属于“正雅典精神”还是“负雅典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说“属于”还是“不属于”。这就像,当我们问“人能不能喂奶?”,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能”还是“不能”,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和男人就不一样,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女人能喂奶但男人不行。所以,准确的回答应该是:近代以前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负雅典精神”,近代以后的西方文明总体上属于“正雅典精神”。
在古代和中世纪,在欧洲大地上流行过的精神体系林林总总,有原始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有斯巴达文化,有罗马帝国的文化,有斯多葛主义,有犬儒主义,有基督教,有卡尔文和路德的新教。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