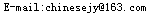余华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语言风格在先锋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在80年代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先锋作家之一。他拒绝用传统的代码去处理生活,试图建构一种背离常规经验的认识方式。他认为,“真实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的无边无际”,“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生活给我提供的东西,在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的一种真实”,“我将为虚无而创作”。[1]他用利刃撕裂了世界的本相,裸呈出它的本质,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隐喻象征世界,文本中弥漫着血腥的杀戮气息及诡异的氛围。余华作为纯然旁观者,对丑恶和暴力纤毫毕见,不动声色地向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否认了人身上出现美好、高尚的可能性。也许与他五年的医生职业生涯有关,也许与他的体验与偏好有关,余华在揭示人性恶方面的确是深刻而近乎残酷。但当读到他90年代两部长篇力作《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时,我们不禁会惊诧于他转变之大之迅速。这两篇具有“闪光质地”的作品,以其明确的非自我重复性及对人的精神维度的独特探索,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心灵视界,同时也在先锋派的革命性将成为明日黄花时,及时有效地激活了余华的创作生命力,使他不仅能充任先锋派文学的干将,也同样能在先锋文学向当代化转型的大潮中独领风骚。
一
读余华的先锋作品,仿佛走进一个暴力和恶的世界,文本中散发着一股股发霉的死亡气息,笼罩着无际的死亡阴霾。他不但对颠覆人们的阅读期待和话语经验乐此不疲,而且对伦理道德、对历史、对常识的反动亦得心应手。余华小说的一个核心语码即暴力。他热衷于描绘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的争斗与残杀,通过特定情境下人的暴力本能的迸发以致相互杀戮让“兄弟怡怡”、“温情脉脉”的面纱无声滑落,以此来否定亲情、友情、爱情,证明人与人之间亘古不变的冷漠、敌对与仇视。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说皮皮摔死堂弟尚属失手的话,那么他对堂弟揍耳光、掐喉管的行为并从中感受到无限乐趣的心态已隐然阐述了人性恶之主题;山峰兽性大发,一脚踢死皮皮,这导致山岗对他的杀害;山峰的妻子则充满恶意地将山岗尸体献给国家以期医生将他零割碎剐,让他死无完尸。在这整个杀戮过程中,母亲始终漠不关心,犹如局外人,只是自顾自怜,热切地盼望儿子们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传统意义上家作为温馨幸福的港湾这一概念在此被解构得体无完肤。《世事如烟》中,90余岁的算命先生不惜一一克死儿子以给自己增寿;60余岁的老妇与孙子同床而怀孕;父亲卖掉六个女儿以牟利,并出售了第七个女儿的尸首,整篇小说阴风惨惨鬼气逼人。《古典爱情》中,饥荒之年即使是昔日娇贵的富家小姐也同样被家人无情地抛弃沦为“菜人”,读至此处犹如走进一个血淋淋的屠宰场,看到一幅残酷狰狞的生存世相。《河边的错误》中疯子挥舞着一把柴刀大开杀戒,让人毛骨悚然,《难逃劫数》则是“一锅阴谋、情欲、凶杀、变态的大杂烩”。《呼喊与细雨》通篇氛围沉闷而压抑,孙广才扮演了一个卑劣、狡诈、贪婪的无赖角色。他将自己的父亲及儿子斥为“两条蛔虫”,无端地嫌恶、虐待。当经过20余天不耐烦的等待终于听到了父亲的死讯时,他不禁“喜形于色”,“如释重负”。小儿子舍己救人,成了英雄,孙广才一心指望凭此资本能荣誉加身,财源广进。梦想幻灭后,他破罐破摔,与大儿子共同出入于寡妇的卧室,并调戏儿媳。家庭之外同样充斥着阴谋、丑恶、陷害与歧视:苏宇凄惨地死去,冯玉青被欺凌,国庆被遗弃,学生与老师私通……人性乖戾、怪诞,被彻底扭曲了。惯常的温情被冷漠与暴力肢解得破碎支离。
余华用绝对冷观的叙述态度和超然物外的叙事语感从容不迫地向我们展示人与同类间的残杀及人的自戕自残,似乎在演示一场人体解剖实验,绝对清晰生动具体可感,这无法不使每位具有正常感情的读者感到惊悸。一段段文字犹如一把把利斧,在砍斫着我们的神经,撕扯着我们的感觉,从可怖的场景中我们窥视到了一个非人的世界。“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2]世界是如此混乱、无序、陌生,人性是如此可怕、可憎、可鄙,那么死亡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死亡这一仪式在余华作品中频频出现,我们无法忽略它的存在。死亡作为暴力的不幸后果抑或必然产物,似乎是克服命定谬境的一种出路。孙广才不仁不义不慈不孝又淫又贪又残暴又无能,他只好可悲地醉死在粪坑里;《一九八六年》中疯子20年后仍无法摆脱“文革”的阴影,他在精神的重荷及肉体的自戕的双重折磨下孑然一身死在街头;东山与广佛毁于自己泛滥的情欲;刑罚专家未能如愿以偿死于自己独创的刑罚,他自缢身亡……。死亡,曾被古典悲剧作家赋予崇高的精神价值,现实主义作家也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对死亡的敬畏,而余华冷冷地告别了死亡之崇高、悲壮等感人色彩,而把死还原给生命本身,由死亡顿悟出生的脆弱、冷漠,历史的虚伪、无聊。在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中,漂浮出一种价值的虚无感,死亡只是一种成规化的游戏,死亡的可能性正在挤压生存的平衡性,而生存又日益丧失其魅力及意义,那么,人的精神家园位于何处呢?这难怪余华在痛悟生存的荒诞本质、人类的荒谬处境后会深深遁入非理性中去,在作品中赫然升腾起一片非理性的世界来。
通过对历史中积淀着的暴力、罪恶的无情剖示,余华慢条斯理地解构着历史。历史不再是绝对真理,它本身也是一种叙事。余华对之追问、质疑,试图揭示其本相。《古典爱情》中,人像食物一样被出卖、被宰杀、被吞吃,这比《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来得更直观,描绘得更细致,因此也就更触目惊心。历史的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淫着血腥的气息。《鲜血梅花》里武林中刀光剑影闪烁不定,是非恩怨纠缠不清,整个武林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风的历史。《一九八六年》中一个在“文革”中被关押迫害而发疯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流浪了20年后又走回了小镇,走进了这个昔日血流成河今日春光明媚的小镇。“文革”的暴行在他脑海中的深刻烙印使他无法与现实亲合,他安详地生活在自己的记忆中,依次在自己躯体上向人们再现古代各种酷刑:墨、劓、宫、大辟,让围观者也让读者感到不寒而栗。余华将这令人发指的一切轻松地置于笔端,“文革”对人的生存权利的褫夺及历史的暴虐在疯子身上得以体认和再现。这就是历史的本相,历史就是由杀戮、暴力、刑罚与荒谬交织而成。所以余华在《往事与刑罚》中毫不怜悯地将历史从昔日权威的宝座上拉下来施行车裂、宫刑、腰斩及点天灯。历史不复是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不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文韬武略,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那样神圣不可动摇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暴力是对历史的一种提纯,一种总结方式,是历史的前进动力,同时也是余华颠覆历史的有力手段。
余华的小说还不遗余力地揭示常识的谬误及罪恶。他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2]常识是人们约定俗成、代代相习的一些知识、经验、道理,是人们感知、认识、判断事物的方式,余华认为生活常识包含着很强的理性内容和庸俗气息,常识并不总是真理在握,他背弃了常识,构筑了一个与常识经验迥然不同的文本世界。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自始至终都充溢着种种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情境,整个过程如梦般迷蒙离奇,游移不定,它用多种可能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义。《河边的错误》写连续杀人案,许亮因为几次连续出现在杀人现场而被常识判断为重要嫌疑犯,他无法忍受这种心理折磨终于自杀了;而真正的凶手疯子却让法律束手无策;马警官不愿让罪犯逍遥法外,击毙了他,却要为此负法律责任;为逃避牢狱之灾,他依计装疯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整个事件就是这样怪异荒诞,令人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常识的怪圈,人们都受着常识的捉弄与嘲讽,而常识在野性面前又显得滑稽可笑,这就产生了一种深切的荒诞感。《四月三日事件》中有一个迫害妄想狂,他总怀疑在四月三日有一个阴谋在等待加害于他,这个阴谋是由他周围的一切人———父母、朋友、邻居共同策划并将合力实现的。他认定现实中杀机四伏,在幻觉中越陷越深,终于爬上列车胜利逃亡。变形的碎片中折射出一个痛苦、焦灼的灵魂。“我”作为理智贫弱者的存在向常识发出了挑战,显示了超验的非理性世界对理性、秩序世界的侵压。余华对常规经验的反拨使旧有价值摇摇欲坠,他穿透了禁锢人们感觉的现实之厚壁,让世界的本真无蔽地显现出来。
余华对固有秩序和权威的挑战还表现在他的文本颠覆及对读者阅读期待的破坏上。《古典爱情》沿袭了古典文学描绘爱情的套路:布衣书生、朱门小姐后花园一见倾心,盟誓切切。我们正等待着出现书生金榜题名与小姐喜结良缘的结局,不料情节陡转直下,小姐在荒年竟成为“菜人”,沦落到任人屠宰的境地,书生心如刀绞却无力救助,只好看着心爱的人在怀中死去。这一幕何其凄惨哀绝,构成了对古典才子佳人小说的巨大反讽。《河边的错误》则可视为对侦探小说的反拨。侦探小说对案件的动因、结果极为重视,层层铺垫之后是令人恍然大悟的结果。这篇小说中也出现了几起凶杀案,颇为扑朔迷离,令读者兴致勃勃,哪知凶手是个毫无理智可言的疯子,他杀人没有任何动机可言。因果链破碎了,警方的忙碌显得狼狈可笑,成了无意义的程式。《鲜血梅花》是对古典武侠小说的戏仿。阮海阔庄重地承担起为父复仇的使命,四处漫游,寻找仇人。当他得知无意中已假别人之手杀了仇敌时,不是欣喜若狂,而是“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怅惘不已。为父报仇本应是侠客最神圣的使命,但阮海阔有仇无恨,漫无目的浪迹天涯,将必然轻飘地化解为偶然,传统的武侠小说在此遭受了一次善意的嘲弄和打击。余华对传统文本的戏仿、对经典话语的解构是他对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颠覆的途径,是他对理性、秩序挑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