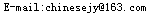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还没出版,就闹得沸沸扬扬,关于余先生在文革中是否清白,是我不能讨论的话题,我也不愿意知道。今年我订阅的《收获》第四期刊登了《借我一生》的前两卷,一直没工夫看,只是在网上经常看见有人拿一个人历史是否清白在做文章。
我以前很不喜欢余秋雨,主要是不喜欢他那种酸劲,一种说不来,却让人不舒服的酸劲。这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天生的对城市文明人有一种敌意。
余秋雨先生在第一卷主要写了他的辉煌家史,请原谅我大量引用余先生的原文:
祖父,“著名民族企业的高级职员”。
祖母,“她姓毛,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这事情细想起来有点好玩,所以人们也就不去细想。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
外公,“朱家可算一个豪门,外公的父亲朱乾利先生由浙东一个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经见过一本印制考究的纪念图集,沈钧儒先生题词评价他是商界泰斗。这可能是悼念期内的夸张之言,却也不至于惹人笑话。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染料市场上发了财。”
姑姑,“刚满十岁就去做童工,这种经历很容易让人天然的倾向社会革命。几年之后,她渐渐长大,成了工厂里罢工的领袖。据爸爸和叔叔后来回忆,种种迹象表明,她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
关于祖上的荣耀,余先生先写了一个故事:余窑主与朱夫人为了保护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熄灭了石窑,也就是越窑,中断了越窑的历史。
余先生没有直接说那两个人就是他的远祖,他借用了一个杭州老人的话:
“你妈妈姓什么?”几年前那个向我讲了南宋末年越窑熄火传说的杭州老人问我。
“姓朱。”我说。
“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说,“余上林一定是你家远祖。他儿子远走他乡,但按照我对他的理解,多少年后还一定会拖家带口地回来。何况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这一带。”
“只有他知道古书藏在哪里,但他至死没说,对吗?”我说。
“对。”杭州老人说。
还有“玉树临风,被除了小媳妇还有更多没结婚的女孩子,团团围住”的叔叔,“他先参加了土地改革,再参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贫困,决定不回上海,选了一家新四军留下的蚌埠东海烟厂,做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及“挺拔、美丽,再加上多年富贵生活的濡养,使她有一种足以指挥街市间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躲闪、羞涩,一派爽利直率。”的姨妈。
我不知道余先生所说的有多少是史实,有多少是臆想的成分,历史学家也不知有没功夫替余先生考证一番。我只是见到一个贵族的后裔站在瓦砾堆上,缅怀他的祖先。“我从前也阔过”,借用一下阿Q的名言吧。
第二卷余先生主要写了在文革中的经历,对于各种细节,我无从知晓,也就没有说的权利,只知道原来拨乱反正时,上海开放的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原来是余先生的功劳。而余先生在政治斗争最残酷时,钻进了“中正图书馆”,“躲进小楼成一统”,失踪了。
当然我们这个民族还得感谢余先生,“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
我不喜欢人写自传,因为除了歌功颂德,粉饰自己,不知他们还会干什么?当然喜欢看一个完美的才子,一个英雄的故事的人,不妨看一下余秋雨的《借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