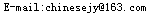发布时间: 2003-4-28 作者:吴思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在历史叙述中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基本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往哪里去?全文章节如下:
一、农民和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二、新思想与士阶层
1、意识形态性的执政集团
2、解释变局的努力
3、被选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毛泽东思想
1、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2、新民主主义
3、社会主义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开明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
一、农民与帝国
1、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表现形态——“暴力-财政实体”[1]。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2]。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有文献可证的中国文明史早期,井田制中的庶人在公田里偷懒。公田里草荒严重[3]。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之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这种困境逼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田和土地自由买卖,公田上的劳役也转变为“初税亩”中的实物。
随着井田制的逐步瓦解,世袭贵族也逐渐被官僚所取代,郡县制开始替换分封制[4]。由秦国发挥到极致的国君集权制度,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凭借这个体制和奖励耕战的政策,秦国将作为主要物质生产者的农民的生产潜力激发出来,将各种人力资源的体力智力和勇气激发出来,并将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聚集在专制国君手中,形成了集中使用的巨大优势。依靠这种优势,秦国在暴力竞争中淘汰列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秦帝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半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确立了秩序,因而深受欢迎。但是,帝国制度在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代理人利益的新问题。同时,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导致了统治集团不受制约的自我膨胀,导致了对被统治者的过度侵害,自耕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沉重的劳役和刑罚制度所取代,帝国的根基破坏了,秦帝国二世而亡。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竞争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这套体系高度适应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不断入侵的地理环境[5],高度顺应众多暴力-财政实体争霸中原的历史演化路径,同时又密切对应着作为自身基础的小农经济。这套高效率的综合性适应体系[6],成为称雄天下两千余年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历史活动主体,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篇章。
2、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西汉总结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7]。
儒家学说比较完美地描述和论证了这种均衡关系。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被皇帝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对公平和正义的看法。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现实的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正式规则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8]。王朝更替是对过度失衡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不得不承担官僚代理制度的弊病。当官僚代理制度以郡县制的面目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正在分封制培育出来的诸侯大夫的战争中流血。官吏代理人对他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分封的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制度。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官吏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像牧人受雇放牧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
小农经济的分散自给特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这两种状态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影响在能力和方向上大不相同,因而在相同的几大社会集团的构成格局中,产生了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秩序。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帝国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分明。在这个过程的末端,则是循环出现的帝国崩溃和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逐鹿中原的军阀混战。而在争夺天下的混战中,最终获得竞争优势的体系,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帝国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时,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帝国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资源竞争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吸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帝国官吏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更大幅度地偏离儒家对基本秩序的规定。最后导致秩序崩溃,天下大乱,人口锐减,直到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收益低于保护或从事生产性活动为止。
帝国无法吸纳自身创造的过剩人口,这是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帝国秩序的破坏与人口压力增加的同步交织确实容易搅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但是,帝国对儒家秩序的周期性偏离与复位,毕竟有别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人口与土地均衡关系的破坏与重建,尽管这两种失衡共同以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为常规的自我校正机制。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3、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间工商业推动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官营工商业以强制手段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资源,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产品和宏伟的建筑,创造出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官营工业生产体系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