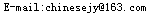基于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所剩无几,这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并且对某些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明确表达对未来的激进选择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激进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当代危机不只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激进行为,安守现状,因为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充当资本主义的替身。僵局迟早要被打破,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思考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替身的主要来源似乎已在其自身历史结果的重压下四分五裂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过多次危机,这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不断地受到怀疑。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遭到各种激进观点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因其对经济剥削和阶级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无法看到在狭隘的经济组织之外还存在别的压迫和剥削。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为如下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一些经济剥削和压迫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另外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诸如此类问题的持续存留,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觉醒了,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宣称提供资本主义的替身,马克思主义者就得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质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看来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未来,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这些问题的时间。全球经济组织的巨变,不仅迫使一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而且引发了对接踵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的质疑。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变了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对所有关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评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这些变化,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被贬低到了社会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势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虽然现在就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人类解放的理想──广义地讲,就是从经济的匮乏中、从社会和政治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的世界形势,而且必须与新的社会支持者的理想相结合,因为他们是伴随? 耪庵中碌淖纯霾摹?nbsp;
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最近面临的空前危机。但同样也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暴露出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缓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质疑──把马克思主义的失落解释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激进批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激进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过去所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激进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点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胆地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进观点的危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次评判,以便把它从其过去历史中挽救出来。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点,以便在思考关于未来的激进可能性时──不管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些缺点。
我将结合当今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新调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为理解当代全球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文本背景。我认为,对于把握这些变化的实质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种被建构到理论中去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alism)。毕竟,现在成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或者说"恶性发展",旺达那·希瓦(Vandana Shiva)这样称它)的整个观念。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妥协、乃至放弃理论的一致性。我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理论必须通过妥协来达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让理论妥协。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论本身或者某种标识理论的特殊理想。
我关于拟定一个解放议程的那些结论适应于当代的世界状况,但不能因此而轻率地把我当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些结论同样也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总的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畴(包括阶级范畴),不仅不能解决解放的问题,而且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我反对用这些范畴来制造理论上的整体化,也反对将其他范畴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我的评论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元理论的时空预设的批评,正是这些预设使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成为一种受制于其原生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并设制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理想的界限。我的结论是,解放的理想必须独立于理论而形成,因为这种理想并不象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所假设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固有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固有的理想因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是有限的。
但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它所指导的革命实践,对于了解这种关于"从理论中获得解放"的争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它所产生的历史经验,我自己的观点就无法产生。我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命运)的分析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启发,同时我也直接引用以不同形式表述的世界体系理论。即便是我引入理论(或理论范畴、或其元理论前提)中去的那些附加观点,也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的产物。为了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我还借助于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经验──我视之为第三世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实例──并用纯粹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实际上,那些附加的观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传统的一部分,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可能不太愿意去领会其中隐含的全部寓意。
这里,成问题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尽管有人硬说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的,但我还是拒绝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体系的整体化做法。这类封闭体系由一种概念简化主义(categorical reductionism)所引导,把所有社会范畴消减成为数不多的几个马克思主义范畴。当然,整体化的做法对于反抗具有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整体化应该超越资本主义,把社会问题同解放结合起来。因为,不管资本主义对于暴露这些社会问题来说是多么重要,但在资本主义问题范围之内终究不会包容这种解放。因而整体化的新模式必须是开放的(也即历史的)而不是被概念预设所限制的。它也不应是一种简单的多元性,因为要它保留对整体性的渴望和在历史地表述整体性的过程中使概念清晰化的需要;它预设具体表述过程中的社会概念不是彼此孤立的──就象它们在抽象分析法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而应具有不可缩减的多重决定性(overdeterminedness),即在历史地演变着的整体性中赋予具体社会概念以相应的意义并且设制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程序。这也同样证明了我关于解放的目标必须独立于理论的主张。道德选择并不必然地隐含在理论中或其即? 嚼吹睦坊肪持校杂诒硎鼋夥诺哪勘晔侵匾摹6獠⒉皇撬嫡庑┭≡褡陨硎俏涠系模徊还芩鞘欠窨赡堋⒛酥潦欠裾业降靡韵韵值姆绞剑庑┭≡褚膊挥ν夥诺奈镏驶肪撤至芽础B砜怂贾饕宥源擞泄疃嗦凼觯欢思岢纸夥诺哪勘辏砜怂贾饕灞匦朐诮夥哦氛讨兄匦露ㄒ遄约海⒆急负冒阉恼逍愿拍罡恢指惴旱恼逍越岷掀鹄础U庵指惴旱恼逍杂锌赡艹鱿衷谡〗夥哦氛牡仄较呱希灾磷钪杖∠淅砺郾旧怼?nbsp;
我想通过对"阶级"的简要分析来说明以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阶级范畴──马克思主义用以进行社会分析的中心范畴──不仅不足以分析解放的条件,而且其简化主义甚至可能成为完成解放任务的障碍。但这不是说社会分析可以不要阶级概念,也不是说阶级概念与对解放目标的表述毫不相关。在目前用于激进社会分析的所有流行范畴(我指的是性别、种族、人种等等)中,阶级范畴对具体的社会认同来说仍是不可化简的。阶级范畴的抽象性,对于揭示那些位于资本生产模式的中心、隐匿于其日常运作假象之后的社会关系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性别和种族之类的范畴,不管我们多么坚信它们代表某种社会结构,却只具有极易辨别的社会的(极端地说,是生物学的)特质。阶级范畴却不同。历史上对阶级进行具体社会表述的各种尝试,为阶级的抽象性提供了广泛的证明。不过,这样的证明因事而异,它们不是出现在易辨别的社会联系中,而是出现于相当抽象的"阶级意识"观念中,而这种观念又极易在日常生活中被更加具体的社会关系所淹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如果作为概念的阶级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主要具有"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意义。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产生和维护这种基于阶级的政治时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即使在阶级政治已经产生出了阶级组织的地方,阶级组织也存在一种使自己脱离其社会支持者的倾向,因为这些支持者不能在一贯的基础上保持团结